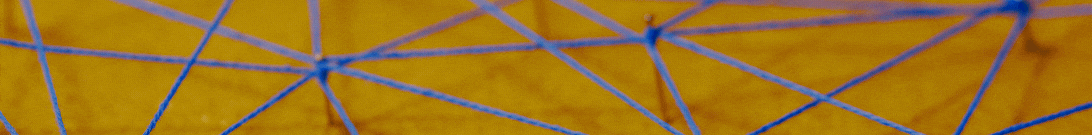羅德里格茲(Tina Rodríguez)童年是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受害者,她多次因為父親虐待母親和她的兄弟姊妹打電話向911報案。父親的攻擊不僅造成她飲食嚴重失調,還讓她深受創傷,經過多年的家庭治療才得以痊癒。然而,這條療癒之路引導她走出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羅德里格斯和毀掉她童年的男人已經和解。
作為她和其他性攻擊倖存者課題的一部分,羅德里格茲邀請她的父親和其他施虐者分享經驗,談懲罰在刑事司法系統中代表的意義。但她的父親認為,比坐牢更讓他痛苦的,是面對自己對家人造成的傷害。
羅德里格茲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舉辦的一場會議中說:「受憤怒或暴力衝動影響但無法控制自己的人,和家暴受害者之間,存在一道文化性責任的鴻溝。」
「尋求安全與正義的犯罪倖存者」(Crime Survivors for Safety and Justice)加州地區經理說:「刑事系統協助製造痛苦,並企圖把我們深鎖在痛苦之中,我們只能依賴教育進行預防和干涉。我們必須負起自己的文化責任,教育我們的年輕人什麼是家庭暴力以及如何防範。」
根據《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20年刊出的一篇報告,在疫情期間,四分之一的女性和十分之一的男性面對親密伴侶或配偶的虐待。未經證實的報導也指出,新冠疫情期間家庭暴力急遽增加。
亞太性別暴力研究院(Asian Pacific Institute on Gender-based Violence)常務理事坎特(Monica Khant)說:「和施虐者一同隔離時,受害者很難獲得資源或幫助。他們很難有時間偷偷到浴室打求救電話,也很難透過電腦獲得需要的訊息,因為許多移民家庭沒有疫情期間必要的網路可用。」
刑事司法系統處理家庭暴力的方式,特別是少數族裔和移民社區的案件,通常從接到911報案電話開始,然後向警方提出投訴,法院再介入發出可將施虐者與受害者分開的禁制令或憤怒管理治療措施,但這些都無法解決暴力的根本原因。
儘管施虐者和受害者必須共享子女監護權,司法一般的處理方式都是拆散家庭,走的並非和解路線,更別提非裔母親害怕警察會介入並殺死她的伴侶
,或移民母親害怕報警會讓家人被遞解出境。
曾代表過數百位家暴受害者的坎特說:「受害者的第一選擇通常不是離婚或擺脫受虐。最好使用社會服務進行和解,而不是使用現有的刑事系統解決問題,這點很重要。」
然而,移民因為有語言障礙或文化差距,資源取得不容易,為了避免「讓家庭蒙羞」,有時會被迫繼續承受暴力。有些施虐伴侶因為疫情失業,因為移民身份沒有資格領取失業救濟金,財務變得較不獨立。
社會問題
羅德里格斯的父親因為虐待家人被判入獄,出獄後,他同意參加修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計劃。羅德里格斯稱這個過程很「殘忍」,充滿許多「露骨且脆弱」的對話。
羅德里格斯說:「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樣,也有過自殺的念頭。」這些碰撞不但幫助她康復,同時激發她領導加州山谷監獄(Valley State Prison)一項家暴防制計劃。
羅德里格斯觀察到:「社會對性別做出職責分配,男性通常被期望要負責養
家。沒有人談過非裔男性承受的壓力,無論他是否受過大學教育,是否有一技之長,但他的膚色可能讓他面試五次後仍被淘汰。他的憤怒來自被壓迫和被工作機會淘汰造成的創傷。」
西語裔男性為了尋求更好的未來選擇移民,背負世代傳承要他們賺錢養家的期望,他們可能因此產生害怕失敗的恐懼,最後出現暴力衝動。
加州終止家庭暴力夥伴(California Partnership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常務理事摩爾歐比(Reverend Aleese Moore-Orbih)說:「我們經常視家庭暴力是個人經驗的結果,其實它是一個社會和文化問題。」
摩爾歐比說:「它代表社會的健康狀況,也代表社會生病的程度。人們經歷過的家暴、性攻擊、人口販賣、兒童虐待,都會對他們造成終身的影響。」
服務受害者超過20年的摩爾歐比親眼看過,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如何從一代人傳給下一代人,讓他們「作為人類無法活出圓滿的自己」。
摩爾歐比說:「婦人、女孩,以及那些自認擁有女性能量的人永遠是最脆弱的。我們談健康的男性氣質,那健康的女性氣質又應該是怎樣?我們都應該成為健康的個體。當我們停止把控制和權力當作一種榮耀來崇拜,當我們停止鼓勵我們的孩子追求權力和控制時,我們的親密關係就會開始產生變化。」
對Train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at Compadres Network創辦人暨總監特羅(Jerry Tello)而言,談到家庭暴力就不能不提到壓制、種族歧視、白人至上主義和世代創傷。他說:「有了解這些議題的計劃嗎?完全沒有!」
特羅出生在一個非裔和西語裔家庭,他和他七個兄弟姊妹在加州康普頓(Compton)長大。他的父親是來自墨西哥契瓦瓦州(Chihuahua)的移民,在他還很小的時候就去世。受到強大男性文化的影響,他沒有為父親的死亡表現出哀傷。
特羅說:「我把悲傷深藏在心裡。為了生存下去,我學會我不能有感覺,因為感覺會讓我變脆弱。」當看到許多朋友的父母被逮捕送走,甚至被槍殺,特羅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痛苦。他說:「我不能哭。」
32年前,特羅和他的心理醫師同事共同創辦了Compadres Network,發展療癒團體,並為年幼孤兒、青少年小爸爸和家庭設計克服困難的課程。
特羅說:「我們決定,療癒第一步要先療癒自己,我們必須恢復作為人的神聖性,我們自己和社區都有解藥。」他歸結:「這個轉型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就是讓自己振作起來。」